《气功师魂穿古今》 章节介绍
《气功师魂穿古今》文笔优美,故事创意不错,可见中跃是下了功夫的,从这里也能看出他的写作和创作能力,非常不错,第2章内容介绍:假女人的噩梦时分、住在宾馆里的柳花明很长时间里都是惊魂未定,不时回忆起原来的自己——于超越、子夜魂穿女司机、再将自己......
《气功师魂穿古今》 假女人的噩梦时分 在线试读
假女人的噩梦时分
、
住在宾馆里的柳花明很长时间里都是惊魂未定,不时回忆起原来的自己——于超越、子夜魂穿女司机、再将自己的尸体抛进长江的惊心动魄的过程。
夜里做梦十有八九也是这样恐怖的场面,挥之不去。
她常常在子夜时分被恶梦惊醒,大叫一声,滚到床下,就像被人扔进滚滚长江……
……
——那是一个晚春的深夜,凉风习习。一个中年男人从一家医院大门的黑影里溜了出来。他身着病号服、白衣白裤,飘然如一具幽灵。
门外小广场上停着几辆龟壳似的出租车,男人来到其中一辆蓝色的丰田凯美瑞车前,朝里窥视了一下。
开车的是个姑娘,看上去很年轻,二十来岁吧,她正戴着耳机在驾驶室里摇头晃脑。男人觉得她的脸异常地白。黑暗中,一张白脸像曝光过度的照片,上面好像没长眼睛鼻子。
姑娘听说男人要去南郊招隐寺,嘴大大地张了开来,像唱意大利歌剧《我的太阳》。她以为眼前的这个男人疯了,要不就是别有企图。一种本能的警觉使她浑身上下都绷直了,语气却尽量装镇定:
“对不起,这么晚了,我去不了。”
男人很聪明,一眼看破了她的恐惧。他忙从身上掏出自己的身份证和工作证递给她:
“我爱人是个运动员,在那儿训练,我去看她。”
姑娘扭亮驾驶室的灯,看了男人的证件,姓名:于超越;职业:教师;……她特别将照片和真人对照了一下,得知这个男人是当教师的,便放心了一些。
“你最好还是坐他们的车吧。姑娘手往窗外一指。”
“我怕,怕他们宰我。”男人轻声说。
姑娘瞟了他一眼:“你知道夜里开郊外车费要加倍的。”
“噢,没关系,一共要多少钱?”男人小心地问。
姑娘顿了一下:“给50元算了。”
“行,现在就给你。”
男人变戏法似的,从白色病号衣的胸口里掏出一叠纸币,捻出一张递给她。
姑娘接过来刚要往兜里塞,恍惚间觉得手里捏的是一张普通的小黄纸,忙瞪眼细瞧——清清楚楚,三个人头,其中一个是知识分子,还戴着眼镜。是钱啊。放在灯光下照照,里面也有人影儿、金属线什么的。姑娘的神色便柔和了许多。
男人拉开车门,坐了进去。姑娘想,这男人怎么像纸做的一样,一点份量都没有?通常乘客上车时,车身都会微微往下一沉的。
车缓缓起动的同时,她问了他一句:
“要车票吗?”
“随便。”男人说。
……
出租车轻盈地拐上了路灯光与树影交织斑驳的马路。晚春的夜风扑面而来。
深夜,马路上人迹稀少,四周显得空空荡荡的。
姑娘没话找话说:“你们当老师的,很少打的,你怎么舍得的?”
男人心想:“一个人死都不怕了,还怕花钱打的?”他没说。怕吓着姑娘。
姑娘见他沉默不语,又起了疑心,问:
“你深更半夜从医院里跑出来干什么?”
“今天是小满。”男人咕噜了一句。
“什么?”姑娘惊慌地问。
噢,男人顿了顿,说:“我是个气功师,对节气很注意。”
“气功师?你不是病人?”
“我是来给人看病的。”
“哦?关节炎会看吧?”
“可以。但要看具体情况。”
男人说话时一动不动,语气生硬。
——气功师都像他这样,像具僵尸?姑娘这么想着,从后视镜里瞟了他一眼,却差点吓得惊叫起来——她明明看见他脸上遮着一张纸!定睛再看时,发现是一副黄色的变色眼镜架在鼻子上,一张脸白得像张白纸,嗖嗖地往外透着冷气……
姑娘不由自主地踩了刹车。
“怎么了?”男人问。
“前面就是天桥,过了天桥就是郊区了。”
“我……姑娘不知怎么说好。我有点头晕。”
他却一眼看透了她的心思:“你太紧张了。我们随便聊点什么吧?”
姑娘摇下车窗玻璃,捋捋头发,深吸一口气,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电子钟:22:45-05.21-2016。
“你真的是气功师吗?”姑娘没话找话地。
“师谈不上。会一点儿。”男人两眼直瞪前方。
“学了多少年了?”
“三十几年了。”
“学的什么功?”
“空灵静功。”
“没听说过。难学吗?”
“难。也不难。”
姑娘从后视镜地观察着他,等他说下去。
男人于是又说:“心能静,能空,就不难。反之就难上加难。”
“哦。你呢?能空,能静吗?”
“开始不能。后来可以。现在……”男人摇了摇头。
“现在怎么了?”姑娘好奇地转过头来。
“说来话长。”
男人深深吸了口气,僵直的身体一软,靠在沙发椅背上。
“说来听听。”
“开始也是我身体不好,抱着治病强身的愿望学气功的。我是大学教师,平时不坐班,有空闲时间,心也静得下来。人家说,穷人没事干,才去学气功呢,那些公仆、大款们整天忙得团团转,哪有心思学这玩艺儿?像我这样的人,学到一定的时候,功也就难上去了。就像跳高一样,跳得越高,就越难提高。你明白吗?”
姑娘点点头。
“何况现在,出了一些事,心更乱了,功大概也会退的。”
“出什么事了?”姑娘好奇地问。
男人深深叹口气。他知道他的肾已经坏了,尿毒症晚期带给他的只有最后几十天甚至十几天的剧烈疼痛。现在要是有十几万元钱换个肾还来得急。可哪来这笔钱呢?
……
现在,整个学校已经为他住院治疗的庞大费用而惶惶不安。学校本来就够穷的,国家规定发的误餐补贴,好几年一直拿不出钱来发。这下好了,有传闻说,他这一病一死,非把明年全校的补贴都吃光不可,老师们只能白白忍受“误餐”的煎熬了。
在这节骨眼上,学校一排宿舍房坍塌了,把十好几人包括他老婆活活砸死在屋内。这事惊动了省里,学校反倒因祸得福,要到了一笔救灾拨款,重建宿舍楼。而死了的人却不能复活了。讨价还价,发一笔抚恤金了事。
那晚上他因为住在医院才幸免于难。
那是一排土坯墙简易房,冬天进风夏天进水,房顶上却架着沉重的水泥梁。房子早就有坍塌迹象,墙肚子一个比一个凸得凶,上级年年来检查都判定是危房,而他们也就这样提心吊胆在里面年复一年地“危住”下去。
他好歹算个小知识分子,有点小知识,知道人活着要对社会有点小用。而现在,他是大家的拖累,是单位的拖累,也是亲人的拖累。他再也不能拖累自己的父母和女儿了。拖累的结果是倾家荡产、自己更惨痛地死。死了还要被人抱怨。
那么,倒不如现在就结束这一切。他的妻子葬在南郊公墓,他现在就是投奔她而去……
当然,这些事,这些话,他不想对任何人说。
……
不知什么时候,蓝色丰田凯美瑞又稍稍启动了。只听见车胎与水泥地面嚓嚓的摩擦声,轻柔如《安魂曲》的音乐。
“我说你用气功给人治病钱一定不少吧?”姑娘又找话说了。不说话她就要打盹了。
“那不能收钱的。”男人说。“收钱治不好的。”
“那何苦啊?”姑娘说。“我听说发功治病要损自己的元气的。”
“有时会。”
“那你靠什么赚钱啊?”姑娘问。“我听说老师都到处找地方上课拿讲课金是吧?”
“有的是。”
“讲一节课多少钱啊?”
“不一定。几十元钱吧。”
“哎哟,讲一天课,唾沫星子溅一碗,还不抵我踩一个钟头油门的,真惨。其实当教师的除了会耍嘴皮子,在社会上绝对是个低能儿。特别是当大学教师的,没人求,没人用的,聋子的耳朵,摆设。”
中年男人重新坐直了身体,姿势十分僵硬。
姑娘浑然不觉,眼睛盯着车灯光闪烁下黑压压的马路,继续发表高见:
“在美国怎么样?谁挣得钱多谁本事大,地位高;没用的废物才不会挣钱呢!幸好当初我没有上学,在体校混了几年,算个初中毕业生,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……
她咯咯笑起来,好像在为她的无知自豪。
“幸好后来我又得了关节炎,我就退出了柔道队,改行学了驾驶——现在你看,这一辆小车就等于是自己的,还不要花钱买,高兴开就开,不高兴开就睡睡觉,打打牌,自驾旅游,快活得跟神仙一样。你猜我一个月能挣多少?”
男人冷笑道:“这算什么。要我是你,想挣钱的话,比你挣得十倍、百倍还多,你信不信?”
“鬼话,我才不信呢!”姑娘咯咯笑道:什么叫“要我是你”啊?你就是你,我就是我嘛。人比人气死人呢!
中年男人转过脸,一动不动地盯着她。从侧面看,她的脸型很漂亮,青春的身材也结实饱满,薄薄的真丝衬衣后面,双峰高耸,波浪般地颤动着……
姑娘被他从上到下盯得浑身发毛,说:“你还是看前面吧,前面有个叉道,走左还是走右?”
中年男人回头的一刹那,他决定改变主意了。他不想死了,不想去山林里“圆寂”了,他要变成这个二十来岁的姑娘,他要这个轻视他的年轻姑娘付出惨重的代价!
……
在山郊野外的出租车里,中年男人做了最后几分钟的沉思默想,最后还是决定要做那件事——也就是与她像夫妻那样进行交接。不带任何情欲,也不追求任何快感,这只是一种仪式而已。就像打开电视机这前要先插上电源一样。
他将双手放在姑娘的脑门上,闭上眼睛,开始平心静气做他的“空灵静功”。他将调动他的“毕生”功力,倾其全部精力,使自己处于一种高度的“空灵”状态——这样,当子时到来的一刹那,他的灵魂就会脱颖而出,进入对方的躯体。
他觉得自己的灵魂仿佛已经飘浮起来,像只氢气球那样,没有份量;忽然又觉得它像只铅球,沉重万分……他如同一个举重运动员举起了超负荷的扛铃,摇摇晃晃地支撑着,力图站稳脚跟,等待裁判亮起那盏成功的信号灯,响起那声成功的信号……
突然,他浑身一震,失去了知觉。
……
浑浊的江水默默东流。星星躲在遥远的云层后面不敢露面。
“她”最后一次低下头,打量着脚底下的男人,也就是自己的尸体。
——于超越,于老师。这具尸体其实才是原来的自己。
“她”依稀觉得他的面容一会儿有几分狰狞,一会儿又有几分安详,像睡着了后,不时被蚊子叮上一口。
这具尸体曾经装载过自己四十几年的灵魂,享受过快乐,更饱受过无数忧患和悲伤。现在,这一切都结束了。“他”要和自己的躯体正式告别了,就像一个人要离开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房子,不再回来。
“柳花明”将地上的男人往江边拖了几步。地上的碎石子残酷地磨割着他的肉,他不再感到疼痛。“她”想了想,还是蹲下身,把这个男人背了起来,走到江边。“她”原地顿了顿,突然用一个“大背包”的柔道动作,将背上的东西干脆利落地抛入湍急的江水里,伴着沉重的一声闷响……
……
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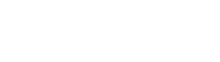
 气功师魂穿古今
气功师魂穿古今
 职场显眼包,我靠摸鱼反杀白眼狼
职场显眼包,我靠摸鱼反杀白眼狼 捡垃圾的爷爷竟然是首富,而我是唯一继承人
捡垃圾的爷爷竟然是首富,而我是唯一继承人 人淡如菊系统?我直接上交国家
人淡如菊系统?我直接上交国家 她的谎言,是我的新生
她的谎言,是我的新生 重回1993,再嫁港城富商
重回1993,再嫁港城富商 催婚?好啊,断你零花钱,看谁先急!
催婚?好啊,断你零花钱,看谁先急! 公司闹鬼,我被迫专治脑残
公司闹鬼,我被迫专治脑残 他闪婚当天,我整了容
他闪婚当天,我整了容 她靠当白月光替身实现财富自由
她靠当白月光替身实现财富自由 辞职后,我成了死对头霸总的心尖宠
辞职后,我成了死对头霸总的心尖宠 烬火重燃:总裁的蚀骨旧情
烬火重燃:总裁的蚀骨旧情 宿命之链:主奴皆归你
宿命之链:主奴皆归你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
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:总裁爹地宠上天
天才萌宝: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
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
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
第一狂婿 桃运透视
桃运透视 总裁的新婚罪妻
总裁的新婚罪妻 鉴宝大宗师
鉴宝大宗师 渔村小农民
渔村小农民 浴血归来:毒妃不好惹
浴血归来:毒妃不好惹 婚礼当天说不嫁?我要疯狂报复她
婚礼当天说不嫁?我要疯狂报复她 烛龙骨
烛龙骨 祠堂里逼我交出家产,他们不知县令已在门外
祠堂里逼我交出家产,他们不知县令已在门外 机械天才
机械天才 我的东莞江湖生涯
我的东莞江湖生涯 完美人生
完美人生 潇洒重生
潇洒重生 国产之光
国产之光 荒岛首富
荒岛首富 巡湖护鱼
巡湖护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