姁是光的意思。风旭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,是在暮春的梨树下。姑娘穿着月白的裙,
手里提着盏琉璃灯,灯光透过花瓣落在她脸上,像落了层碎雪。他刚从许夫人的宴上脱身,
嘴角还带着被酒渍染透的红,听见她对卖花翁说:“我叫姁,女字旁加个句读的句。
”卖花翁咂舌:“好名字,像太阳刚出来那时候的光。”风旭藏在梨树后,
摸着自己腕上的青痕——那是今早许夫人用玉簪划的,她说“你这细皮嫩肉的,
就得留点印才好看”。他看着姁转身离去,琉璃灯的光晕在石板路上拖出长长的影,
突然觉得,原来光真的是有形状的。一、假面许家的高门像头巨兽,每天吞吐着珠光宝气,
也吞噬着不见天日的阴私。风旭穿着锦缎长袍,从侧门走进来的时候,
总会引来下人们的侧目——他们看他的眼神,像看笼里的金丝雀,好看,却没骨头。
“风少爷来了。”账房先生谄媚地笑,递上账本,“这是本月的红利,许夫人说让您过目。
”风旭接过账本,指尖划过“风旭”二字。这两个字烫得他指尖发疼,
仿佛下一秒就要在纸上烧出个洞。他哪是什么少爷,不过是许夫人豢养的小倌,
是许家公子许浩买来解闷的玩意儿。风家早就没了,当年父亲赌输了家产,
母亲卷着最后一点银钱跑路时,连他腕上的银镯都扒走了,
只留给他一句“你活着也是累赘”。“放着吧。”他淡淡开口,声音里淬着冰。
这是他练了三年的腔调,像模像样地模仿着真正的世家公子,
却总在无人处泄了气——就像此刻,他转身走进偏院,撞见许浩靠在廊下,
手里把玩着条黑皮鞭子。“回来了?”许浩笑起来,左眼角的疤跟着动,
那是去年风旭逃跑时,被他用马蹄铁砸出来的,“娘说你近来总往外跑,
是看上哪家的姑娘了?”风旭垂眸:“不过是去茶楼听戏。”“听戏?
”许浩的鞭子突然缠上他的腰,猛地收紧,“我怎么听说,
有人看见你跟刘家的**在梨树下说话?”风旭的后背撞上廊柱,疼得闷哼一声。
他闻到许浩身上的酒气,混着马鞭的腥,像极了那年把他从青倌楼拖出来的味道。
那天许浩也是这样笑着,捏着他的下巴说:“风家的嫡子,沦落到给人唱曲儿,
不如跟我回家,我保你衣食无忧。”他以为的救赎,不过是从一个泥潭,跳进了更深的渊。
“公子说笑了。”风旭压下喉间的涩,挤出个笑,“刘家**是许夫人的远亲,偶遇罢了。
”许浩盯着他看了半晌,突然松开鞭子:“也是,你这种人,哪配得上人家。”他转身离去,
靴底碾过地上的梨花,碾得稀碎,“今晚娘要设宴,穿那件孔雀蓝的袍子。”风旭站在原地,
看着满地残花。他想起姁的琉璃灯,想起她说“我叫姁”时眼里的亮,
突然抬手给了自己一巴掌。脸颊**辣地疼,却赶不走心里那点龌龊的念想——他想再见她,
哪怕是以“风少爷”的身份,哪怕只是说句谎话。二、初见再遇是在城西的书斋。
风旭正拿着本《南华经》装样子,听见身后传来清脆的声响:“店家,有没有《女诫》?
”他回头,看见姁站在书架前,月白的裙角沾着草屑,像是刚从城外回来。
“姑娘也喜欢看书?”他合上书,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自然。姁转过身,
看到他时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:“是风公子?那日多谢你提醒我梨花开得早。
”她的笑里带着点憨,像偷喝了蜜的孩童,“我叫姁,你呢?”“风旭。”他报上名字,
指尖微微发颤,“姓风,单名一个旭。”“风旭,旭日照常的旭?”姁歪头看他,“好名字,
像清晨的太阳。”风旭的心猛地一缩。清晨的太阳?他这种活在阴沟里的人,
连月亮都照不进来,哪配得上太阳。他别开脸,看见她手里的布包露出半块桂花糕,
突然想起今早许夫人用银簪挑着燕窝喂他,说“这东西补身子,你可得多吃点,
不然怎么伺候人”。“姑娘是来买《女诫》?”他转移话题,目光落在书架最高层,
“那书太闷,不如看看这个。”他伸手取下本《山水志》,里面夹着张画,
是他昨晚趁许夫人睡熟时画的——城外的桃花开得正好,像烧起来的云。姁接过书,
指尖碰到他的手,像被烫到似的缩回:“公子也喜欢画画?”“闲来无事罢了。
”风旭看着她翻开书页,画里的桃花映在她眼里,突然觉得那点偷偷摸摸的念想,
像藤蔓似的缠上了心。他想说“我不是什么公子”,想说“我住在许家的偏院,
每天要给一个半老的妇人请安”,可话到嘴边,却变成了:“明日我要去城外写生,
姑娘要不要同去?”姁的眼睛亮了:“可以吗?”“当然。”风旭笑得坦荡,心里却在发抖。
他知道这是在玩火,许家的人要是知道他私会女子,
下场不会比去年那个逃跑的小倌好——听说那人被打断了腿,扔进了乱葬岗,
连块棺材板都没有。可他还是想再看看光。哪怕只有一天。三、灼痕城外的桃花开得疯,
像泼了漫天的胭脂。风旭支起画架,看着姁蹲在花树下,小心翼翼地数花瓣。
她今天穿了件水红的裙,衬得肤色像玉,发间别着朵白蔷薇,是他今早特意绕路去花店买的。
“你看,这朵有七片花瓣。”她举着花跑过来,鼻尖沾着点粉,
“书上说七瓣蔷薇能带来好运。”风旭接过花,别在她耳后:“那祝你好运。
”姁的耳尖红了,转身跑回花树旁,裙角扫过草地,惊起一串粉蝶。风旭拿起画笔,
手却不听使唤——他画不出她眼里的光,画不出她笑时嘴角的梨涡,
更画不出自己此刻的心情,像被投入石子的深潭,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“风公子,
你看那边!”姁指着远处的山坡,“有羊群!”他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,突然僵住了。
山坡下停着辆马车,车帘掀开一角,露出许夫人戴着金护甲的手。风旭的脸瞬间白了,
抓起画架就往姁身边跑:“我们得走了。”“怎么了?”姁被他拽着跑,
发间的蔷薇掉在地上,“出什么事了?”“别问了!”风旭的声音发颤,
他能感觉到背后有两道冰冷的视线,像毒蛇的信子,“快跟我走!”他们躲进半山腰的破庙,
庙里的香炉积着灰,神像的脸被熏得漆黑。风旭靠在门板上喘气,
听见姁小声问:“你是不是……惹了什么麻烦?”他看着她清澈的眼睛,突然想坦白。
想说他不是风少爷,想说他是许家的玩物,想说刚才那个坐在马车里的女人,
能轻易捏碎他的骨头,更能轻易毁掉她这束光。可他说不出口。他怕看见她眼里的震惊,
怕她像躲瘟疫似的躲开,更怕自己再也见不到这束光。“是家里的事。”他低下头,
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,“我父亲欠了债,债主找上门了。”姁沉默了片刻,
突然握住他的手:“没关系,我有钱。”她从布包里掏出个钱袋,倒出几枚碎银,
“虽然不多,但可以先应急。”风旭看着那几枚碎银,突然笑出声,笑着笑着就红了眼。
他这双手,接过许夫人的玉镯,接过许浩的鞭子,接过无数带着屈辱的赏赐,
却第一次觉得烫——这是干净的钱,是带着光的钱,他不配碰。“谢谢你,姁。”他抽回手,
擦了擦眼角,“但我不能要。”那天回去后,许夫人什么也没说,只是让他跪在床边,
看着她慢条斯理地擦拭那支黑皮鞭子。烛火在她脸上投下沟壑纵横的影,她说:“风旭,
你知道什么东西最不经玩吗?”风旭低着头,看见鞭子上的铜环映出自己的脸,苍白得像纸。
“是有了念想的东西。”许夫人的鞭子突然落在他背上,“比如去年想逃跑的你,
比如现在惦记着刘家丫头的你。”四、沉沦风旭开始频繁地见到姁。有时是在茶楼,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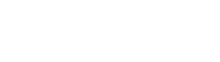

 邻居男神拆了我的私密快递
邻居男神拆了我的私密快递 被堂姐抢走共感佩剑后,我笑了
被堂姐抢走共感佩剑后,我笑了 妄图霸占我房子的同事
妄图霸占我房子的同事 惨死352次后,我和天道反杀作者
惨死352次后,我和天道反杀作者 离婚后我成了前夫高攀不起白月光
离婚后我成了前夫高攀不起白月光 萧麒岑雪
萧麒岑雪 儿子拿我骨灰做烟花
儿子拿我骨灰做烟花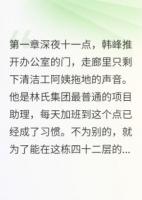 妻子和情夫的对话,被我录了下来
妻子和情夫的对话,被我录了下来 未婚夫青梅烧我功勋祠堂爆改狗坟,我当场退婚
未婚夫青梅烧我功勋祠堂爆改狗坟,我当场退婚 杀手总裁翻车后,军医逼我喝毒酒
杀手总裁翻车后,军医逼我喝毒酒 代管280万高温末世基金后,我赔上了命
代管280万高温末世基金后,我赔上了命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
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:总裁爹地宠上天
天才萌宝: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
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
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
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
总裁前妻要逃跑 天道有轮回
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
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,我的福报来了
九十九岁那年,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,却被女总裁表白了
相亲走错桌,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
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
开挂人生
《夜尽天不明》好像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一样,就是喜欢该类文章,在这里推荐给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最后夸赞一下火洋君主,他的构思能力和写作能力是很优秀的,叫人惊叹。